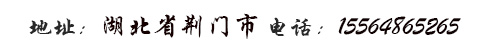贵州作家胡德江散文母亲的春耕
|
第期 贵州作家 作者小档案胡德江,男,生于年,贵州省普定县人,公务员。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散见《山花》、《文艺报》、《中国作家》、《贵州作家》、《散文选刊》、《中国散文家》等。有作品在中国作家杂志社、散文选刊杂志社、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年会等举办的征文赛事中获奖。系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 母亲的春耕立春,母亲开始估摸农时春耕,把珍惜春光时节播种庄稼看成一个年头的头等大事。 立春这天,母亲要打春,一方面要把家收拾干净迎春好过年,一方面要奉供天地保佑春回大地春耕好收成。母亲崇拜天和地,那些年,母亲凭靠勤劳的双手,凭靠老天风调雨顺,凭靠土地肥沃生长庄稼,然后把持一家人的日子过平安。立春要抢春,母亲催我早起,叫我上后山去砍一捆青竹回家来打春。母亲说,趁世人没起床,要赶在前头打春。春耕秋收,心想事成。一大早,厚厚的积雪包裹着山野村庄沉睡,世人还没出门,我就早起磨刀,清脆的磨刀声响彻立春的雪天。我走出家门,留下的一串脚印,我心里感到有个好兆头爬上头顶。上山砍下一捆带雪的竹,我如获似宝一股子劲跑回家,把打春的青竹双手捧给母亲。母亲含笑开始打春,用我抢在世人前头带回家的青竹,一遍一遍清扫家里的扬尘。母亲打春的时候,一直笑着,偶尔扬尘落在眼里,母亲揉眼睛揉出眼泪,我问母亲为什么又哭又笑,母亲说:“儿抢春回家,妈打春高兴。” 真的有个好兆头,母亲打春的时候,有太阳照着雪光,照进我家屋室,家一下子洁净起来,亮堂起来。接下来,母亲要供神龛,神榜是“天地国亲师位”,母亲要供天地,母亲在之前把五碗包谷、稻谷、高梁、小麦、小米育成青青的秧苗,郑重其事用五谷杂粮奉供天地,保佑开春五谷丰登。恰逢立春过年的时节,母亲除了供“天地国亲师位”,还要供毛主席、邓小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老家神龛上有母亲亲自挂上的毛主席像和邓小平像,每年春节,母亲都要扭一大坨糯米粑供毛主席、邓小平。母亲认为,农民种的地,是毛主席给的。农民有口饭吃,是邓小平给的。母亲这种认识和行为至今一直影响着我的人生观和道德观。 雨水节气,山村还在降雪。母亲认为降雪是上乘的雨水,滋养庄稼很灵。母亲接下来要做一件神秘事情,就是泡谷芽。母亲说:“谷芽泡得好,娃娃吃个饱。”意思是说,为了保证大田育秧的出芽率,母亲要泡谷芽,确保出芽率高,育壮苗,稻谷才会丰收,我们才有大米饭吃。母亲在家用一个大土缸泡谷芽,那年头还没有杂交水稻,母亲用的种子,是她收割谷子的时候,一穗一穗筛选出来的。泡谷子的水,母亲称之为圣水。那时候用水很困难,不像今天扭开水龙头就是哗哗淌的自来水,那时候的生活用水是蓄起来的屋檐水。母亲用来泡谷子的水,不是屋檐水,而是大雪天深山里的井水。母亲说,雪天里的井水才是圣水,是天地诞生出来的,没有沾染烟火扬尘,泡出来的谷芽生命旺盛。母亲亲自到十来里路的深山井里去挑圣水,大雪天,通往圣水的山路被积雪封住,为了打上第一桶圣水,母亲早早出门,一往无前,雪路上只留下她一个人的脚印,只看见她一个人的背影。泡谷的水缸大,要三挑水才能装满。母亲挑那三挑水,踩着滑雪偏偏倒倒大半天,才能把缸挑满。母亲泡谷子的时候,不许人看不许人说话,母亲一把谷子一把谷子放进缸,一瓢水一瓢水舀进缸,嘴里念念有词,但听不清念的是什么,我们大气不敢出,更不敢张声。母亲动作神秘,样子神化,好像要演变出什么稀奇东西。母亲说,圣水谷禾,是在神龛上许愿的,杂人看了说了,就不灵了。 泡谷是母亲迎春过年的一件大事,比做年夜饭还重要。泡好谷芽,马上就要过年,母亲马上叫我写春联,那时我还是个学写字的娃娃,但是母亲要我亲自写春联。她请隔壁徐三爷爷出春联,徐三爷爷知书识礼,很看重母亲处世做事,他慎重其事送给母亲一对春联,我规规矩矩照着写上:“耕读两不闲,胡门有大福”。横批是:“人勤春早”。 惊蛰,春雷脆响,万物鲜活。母亲忙活起来。母亲把泡好的谷芽背下水田撒播。然后开始蓄肥,那时为了蓄积春耕肥料,母亲专门编制捡肥的粪箕,一天到晚,母亲提着粪箕到处窜寨子,捡牛粪猪粪。母亲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也跟着提起粪箕蓄积肥料。那时候我们不嫌捡粪是丢丑。母亲说,懒惰才是丢丑。在母亲的影响下,我至今保持着吃得苦下得烂的本事。母亲为了蓄积充足的肥料,到人家请求耕牛来踩圈。牛踩圈,就要喂养好牛,牛才会有劲踩才会产生粪便。母亲每天早起晚睡,割草喂牛,割苦蒿垫牛圈。我除了放牛外,还陪母亲割草,为的是让牛多排一堆粪便做肥料。 牛圈里的粪蓄积满了,要背放到田间地头发酵备耕。我们这里是老高山,粪要用箩筐一箩一箩背上山,爬一天坡,一人一天也只能背三五箩。母亲拿自己当男人使,背粪爬坡,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一天下来,衣服扭得出汗水。我家一坡地,母亲要背一个星期的粪,有时甚至要背十来天,才能背满一坡地。春耕的肥料备好了,然而母亲的腿脚肿了,腰身伤痛了,晚上母亲睡不着觉,在床上打滚呻吟。那时我们还小,害怕母亲痛苦呻吟,只能躲在被窝里哭泣。 春分时节,布谷声声。山野春耕热闹起来,四处传来牛叫声和男人们耕牛的吆喝声。母亲背起包谷、黄豆、老瓜、葵花、花豆等种子,爬坡播种。母亲跟在父亲背后播种,父亲犁出一铧地,母亲就紧跟着播一铧地,老两口配合自如,好像有生以来他们结合就是为了配合一样。春天里,父亲母亲耕作的泥土,在鲜明的阳光下翻晒着,蒸发的地气,有股清香的味道。这种味道让我仿佛看到,绿满山野的包谷林,包谷出天花挂红帽,包谷叶拍打着饱满的黄豆、花豆和老瓜,金色的向日葵在包谷林里昂起头,兴高采烈地笑…… 谷雨节气,母亲忙完春耕大季,抢着忙春耕小季。母亲的春耕小季是家门口的一块园子地。大概一亩左右,母亲栽培这块园子地,像描绘一幅画卷。母亲先是在地坎周围种上一圈西红柿,然后在西红柿后面又种上一圈包谷,好像在为一幅画点缀镶边。然后,母亲把园子分成五厢地,每厢地种上白菜、辣椒、茄子、豇豆、大蒜等蔬菜。夏天,园子地里的西红柿、辣椒、茄子、豇豆开花,一派繁茂,惹来纷飞蝴蝶,惹得儿孙们跑进园子地里玩耍,母亲在园子边上叫骂。为了盘活园子地的蔬菜,母亲是抢着雨水栽培的,岩山地块土脚浅,下雨跑水不坐水。因此,只要春雨降临,母亲就冒着春雨栽种蔬菜。母亲一进园子,脚就生了根,直到春色满园,直到果实飘香。母亲种一季蔬菜,够我们全家吃上一年四季。我搬家进城十多年,母亲时常给我送来园子地里的新鲜蔬菜,其实,一篮子蔬菜,在城里不值几个钱。但是,年老的母亲牵挂她的儿子,为了让儿子能吃上一口新鲜蔬菜,哪怕拖着老弱病残的身体,绕山绕水也要进城为儿送蔬菜。母亲晕车,进一次城,要呕吐几回,要躺床半天,我劝母亲不要再送了,好好保养身体。母亲就是不听,照送不误。有时候,母亲甚至送来亲自上山采摘的春芽和亲自做的毛香粑。母亲说:“小时候你们最爱吃这些了。”是的,小时候,每逢春天春芽、毛香生长出来,我们就开始馋毛香粑了,母亲不管春耕有多忙,总要抽闲等空做毛香粑给我们吃。“毛香粑,甜又香。春天里,爹娘忙。娘打粑粑,爹采毛香,吃得嘴巴甜又香……”我想儿时梦中的歌谣。 现在,我们一个个成家立业了,日子也好过起来了,然而母亲老了,累得一身劳伤病。我劝母亲和我们住,好照料。母亲和我们住不了几天,说楼层高,不着地,住着心悬着,还不如在家种地踏实。我想母亲是怕连累我们。老家的地全都退耕还林了,至于家门口的那块园子地,前两年家乡搞小城镇建设,早已经被征用了。我记得征用那块园子那天,母亲闷闷不乐,在家门口坐了一夜。第二天天不亮,母亲收捡一些盆盆罐罐,下园子地里装土,然后一一摆放在院坝上,开春,母亲就在那些盆盆罐罐里种上包谷、西红柿、辣椒等农作物,有几个大大的破砂锅,母亲种上鸡冠花。开花时节,更多的是清明前后,我总是看到母亲坐在院坝上,脸上露出一丝温凉的微笑…… 母亲的中秋三十年前的中秋月,挂在老家石板房上,离家那么近,离我们那么近。 那一天,我们守着月亮,等爹妈从地头收工回家。邻家娃娃们都捧着月饼、包着葵花跑进院坝吃了。我们坐在门坎上,坐也坐不住,张着嘴巴翘首盼望月光底下出现爹妈的身影,不时瞅着邻家娃娃手上的月饼,吞口水舔嘴皮。终于,看见爹妈的身影在月光下出现了,爹妈背着一箩筐包谷,箩筐边缘插着包谷杆。我们一下子围过去,爹妈给我们一人一棵包谷杆,包谷杆甜又脆,我们大嚼起来。爹妈下地收包谷,总不忘砍一捆包谷杆带回家哄我们。我们吃着包谷杆,在邻家娃娃面前炫耀,哄邻家娃娃手里的月饼和我们交换包谷杆。 爹妈忙活路,已经忘记过八月十五。我们吃着邻家娃娃哄来的月饼,爹妈才知道过节。老妈翻箱倒柜,搜寻好吃的东西。老妈费力搜寻半天,终于在柜子海底角角搜出一包东西,老妈说是点心,是为哥哥说媒讨媳妇留着的。我们眼巴巴瞅着点心,点心用红纸包着,可以闻到里面散发出来的的甜香。我们瞅着老妈,老妈一下子做出决定,捧着红纸包对着月亮,说一句:”月亮婆婆瞅见的!”老妈打开红纸,点心是五个红糖饼子,在那个时候,这种红糖饼子卖一角二分一个,能买得起吃得起已经够奢侈了。过八月十五,能一口气吃够红糖饼子是我梦寐以求的事。老妈手捧五个红糖饼子,瞅着月亮,面对我们七个姊妹,一人一个不够分,老妈索性分给幺弟幺妹一人一个,我们做大的一人半个。我们吃月饼的时候,老妈悄悄走出家门,捡包谷晒院坝。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中秋,爹妈好像没有吃过月饼,说吃月饼是娃娃们的事,大人不吃月饼。 老妈的月饼,是点心,是深藏在每个中秋角落里的心愿,老妈一半一半掰开,把美满香甜分给我们,融合一轮满满的月。我梦想,将来要背一箩筐红糖饼子回家,做老妈的点心。 回头看今天,我吃过上千元包装的月饼,表面上看华丽贵气,但味如木渣,远不如过去红纸包的红糖饼子香甜,感觉不到离月亮那么近。 月光辉辉,石板房泛着银光,石院坝泛着银光,整个寨子泛着银光,中秋的夜晚亮如白昼。在院坝上,人的影子,狗的影子,树的影子,灵动鲜活,形影不离,相依为命,亲切如故。回头看今天,月亮好像暗了许多,月光不如从前那么清澈、那么纯洁,如今的月亮还能照出那种生命亲切、美丽生动的影子么? 老妈爱在洒满月光的院坝上做活路,从山上地头收回来的包谷,晒了整个院坝,散发着新包谷的香味,散发着月光的香味。老妈坐在院坝上收拾包谷,脸上挂着香甜、满足的笑容。我们陪着老妈做活路,听老妈摆白(摆故事),老妈爱摆爷爷、奶奶、老祖公、老祖婆受苦受难养育儿女的故事。老妈如吟如唱,如泣如诉,故事绵长悠远,魂牵梦绕,激荡着我们小小的心田。有时老妈摆不下去了,一阵子沉默,只见她脸上挂着几颗泪滴,在月光下闪亮。直到现在,老妈还一直把我们当娃娃,见到我们,就摆过去爷爷、奶奶、老祖公、老祖婆受苦受难养育儿女的故事。而我们,总是听不够这种诉苦的故事。老妈摆苦,不是她老糊涂喋喋不休诉苦要我们懂得孝道。而是让我们记住,不管什么时候,要吃得苦不能忘记苦,大爱大道大恩大德都是在苦中产生的。老妈摆苦,让我在生命途中有至亲至爱的人相伴,让我任何时候吃得了苦而立于不败之地。席慕容有一诗句:“故乡是一只悠远的清笛,总是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而中秋的母亲就是一轮亲切、圆满的月亮,照亮我生命中的每个角落。 夜半三更静,明月当空照。老妈让我们回家睡觉,她要留下来守院坝上的包谷。老妈说,地头的包谷没让人偷走,可不能收进家门口让人偷走了。我们争先扶老妈进家上床,代替老妈守包谷。 院坝上,狗的影子不见了,树的影子不见了,月光照在包谷上,泛着一片耀光。我们睡在包谷旁边的草垛上,呼吸着包谷的香味,呼吸着月光的香味。中秋的月光是母亲温暖的棉被,让我们不知不觉进入梦乡。我梦见背着一大箩筐红糖饼子回家,献给老妈做点心,让母亲开心、安心。 然而,在外读书、工作,以致成家立业十几年,我始终没有抽空回老家和老妈过中秋。老妈是一轮明月,照亮我的人生路,照亮我生命的每个角落,特别是我人生途中的每个夜晚,老妈总是像一轮明月,照亮那些阴暗的夜路,使我不至于胆颤受怕,暗中摔倒。而每个中秋,我给老妈什么呢?多少个没有我们的月夜,老妈只能守着老家石板房上的月亮,重复她那一遍又一遍的老白话,然后叨念我们的名字! 多年以后,我终于抽空回家和老妈过中秋。老家石板房上的月亮依然大又园,明又亮。白白的月光洒满石院坝,只见老妈手捧一大个红纸包,呆呆地站在院坝上,守望着。她头上的头发全白了,比月光还白。老妈瞧见我们,脸上盈满香甜、满足的笑容,老妈面对月亮自语:“点心点心,娃娃回家,要吃点心!”我接过老妈手上的红纸包,打开一看,是十二个红糖饼子!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想,老妈的中秋,是儿的中秋,老妈从来就没有中秋,老妈从来就把我们当成长不大的娃娃。老妈不吃月饼,吃月饼是娃娃们的事!老妈的中秋,是为儿女们准备的一份点心,藏了又藏,守了又守,每当明月挂在老家石板房上的时候,就盼儿盼女回家来,分点心…… 今年,哪怕是天垮下来,我也要赶回老家过中秋。 贵州作家·指导委员会主任:欧阳黔森副主任:高宏孔海蓉李寂荡何文杨打铁王华赵朝龙戴冰禄琴唐亚平赵剑平黄健勇韦文扬苏丹喻健姚辉主编:魏荣钊执行主编:杨振峰贵州作家以展示贵州作家创作成果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nzixina.com/lzxylzy/8205.html
- 上一篇文章: 论著胆囊息肉恶变的危险因素分析陈少华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