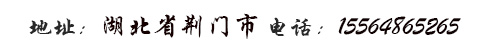谷建胡方平生平及著作考訂
|
胡方平生平及著作考訂 谷建 本文通過分析有關宋末元初《易》學家胡方平較爲可信的相關資料,對其生平事蹟有所訂正;根據其著作《易學啓蒙通釋》之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影元鈔本所載胡方平自序,對《易學啓蒙通釋》一書編刊始末加以考證;根據清嘉慶十七年慶餘堂刊本之序跋及異文,討論所謂“新安槧本”異文之來源,冀明其書之版本源流。 胡方平,宋末元初人,號玉齋,學者稱爲玉齋先生,徽州婺源梅田人。胡方平生長於朱熹故里,學宗朱子,有《易學啓蒙通釋》傳世,專爲發明朱熹《易學啓蒙》之旨,詮釋其象數《易》學。長子胡一桂,字庭芳,號雙湖,承其家學,撰《易本義附錄纂疏》及《周易本義啓蒙翼傳》等,是當時《易》學名家,《元史·儒學傳》有傳。由於胡方平畢生隱居鄉里授徒著述,其學術成就與名氣又不及其子,故歷代傳記資料僅寥寥數語,且輾轉相襲,其中難免訛誤。而《易學啓蒙通釋》一書乃集胡方平畢生之精力而成,在《易》學史上亦佔有一席之地。明代楊士奇曾云“朱子《易學啓蒙》,惟胡方平本最善”,足見其發明朱子學之功。關於其人其書,雖不乏專題研究,然多就此書思想內容言其成就,對於其編刊流傳始末,因資料所限,多語焉不詳,未能明其源流。今試考察胡方平相關資料,特別是年代較早相對可信者,如其子胡一桂著述、一桂門生董真卿著述、元代方志、明中葉地方文獻總集等,並擇《易學啓蒙通釋》二種版本考證其編刊始末,通過文本比勘,梳理版本源流,逐一考訂如下。 一、生平事蹟訂補 胡方平傳記今存最早者,出自元至元間汪幼鳳所撰《星源縣志》,此志雖已難覓,幸明弘治初休寧程敏政所編《新安文獻志》及正德、嘉靖間休寧程曈所編《新安學系錄》中皆收錄此傳: 胡方平,婺源人。曾伯祖昂,政和間由辟雍第,嘗與朱韋齋有同邑同年之好。曾祖溢,紹興初復繼世科,因伯氏交於韋齋,獲聞《河》、《洛》之論,而朱子則世好也。方平早受《易》於介軒董夢程,繼師毅齋沈貴珤。沈實介軒上游,而介軒乃盤澗從子,得其家傳者。盤澗受《易》於朱子之門最久。方平研精《易》旨,沈潛反覆二十餘年,嘗因文公《易本義》及《啓蒙》注《通釋》一書。又《外易》四卷,考象求卦,明數推占。又有《易餘閒記》,其言曰:《本義》闡象數理義之原,示開物成務之教。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而設者歟!象非卦不立,數非蓍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足以演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衍於蓍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其間又多發造化尊陽抑陰之意,《易》之要領,孰大於是!明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也。 此傳介紹胡方平之籍貫、家世、師承及學術,其後有關胡氏之記載均由此而來,並有所增刪,甚至加以發揮,其中難免存在誤記。 例如程曈便於此傳下附小注云: 《宋史》本傳云方平學精於《易》,得文公源委之正。 又加按語云: 先生名允,字方平,一號潛齋,見於《翰墨全書》,可考也。《縣志》、史傳皆逸其名,《易經大全》“先儒姓氏”乃兩出之。 寥寥數語,卻舛誤百出。其一,《宋史》並未給胡方平立傳,所謂“學精於《易》”、“得文公源委之正”,原出自《元史》卷一八九,係胡方平子一桂本傳,而程曈卻誤植於方平。其二,《周易大全》,當係明初胡廣等人奉敕所編之《周易傳義大全》,其“引用先儒姓氏”中既有“玉齋胡氏方平”,又有“潛齋胡氏允”。然程曈按語不取此說,而是據《翰墨全書》提出“名允,一號潛齋”之說。《翰墨全書》當即《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是元初建陽人劉應李所編之民間交際應用類書。劉應李曾與熊禾、胡一桂同處武夷山中讀書,切磋學問十餘年,可稱學友。程曈取其說,而不信年代較晚《周易傳義大全》,亦在情理之中。然今檢胡一桂門人董真卿《周易會通》,其卷首“引用諸書群賢姓氏”與《周易傳義大全》同,胡方平與胡允兩出: 胡氏方平,玉齋先生,徽州婺源人。師鄱陽介軒董先生、毅齋沈先生。著《易學啓蒙通釋》,至元己丑自序。 胡氏允,號潛齋,饒州樂平人。《易》解曰《四道發明》。 董真卿嘗隨胡一桂讀書武夷山中,關於其師祖胡方平的記載應更爲可靠。相形之下,《翰墨全書》卷帙浩繁,內容博雜,泰定年間又經建安詹友諒修改,多有增刪,且多由民間書坊刊印,誤記、誤改、誤刻之可能性遠大於董書。 董真卿稱方平爲玉齋先生,此號亦見於同時代學者之序跋文章,應無可置疑。然後人傳記中又有方平“字師魯”之說,初見於《(弘治)徽州府志》,不詳所據,後世亦常沿用。今檢明天順四年刊休寧金德鉉所編《新安文粹》,其卷二收有胡一桂《贈師魯學易序》一文。《新安文粹》與《新安文獻志》編纂時間略有先後,收文論博雖不及後者,然此文則《新安文獻志》未見,一桂文集亦失收。據文意,此“師魯”當係一桂學友東山汪淮字。如方平果字師魯,而一桂在學友與父同字的情況下,竟能毫無避諱,似有不妥。此“字師魯”說,只可存疑。 《易學啓蒙通釋》之外,胡方平尚撰有《外易》四卷,據傳記云,當爲“考象求卦,明數推占”之書。今胡一桂《周易本義啓蒙翼傳》中有《卦爻言數例》一文,文末小注云“見先人雜著”,此雜著不知是否即指《外易》,惜今已不傳。“外易”二字,後人多有寫成“外翼”者。至於《易餘閒記》,實際上只是一段文字,《(弘治)徽州府志》及《新安文獻志》皆作爲胡方平文章收入,題作《書易啓蒙後》。而後人竟以爲書名,甚至出現“一卷”之卷數,皆係望文發揮,毫無憑據。 關於方平之交游,胡一桂《周易本義啓蒙翼傳》有云: 鄱陽汪深所性,先人私淑之友也,嘗作《占例》。 《新安文獻志》亦稱: 汪所性深,歙人,遷鄱陽。與胡玉齋友善。嘗著《易占例》。 可知鄱陽人汪深乃方平友人,亦通《易》。其著《易占例》今佚,惟汪深自序一篇存於《新安文獻志》。 關於方平門人弟子,見於記載者有二,一名吳霞舉,一名李偉,均出自《(弘治)徽州府志》: (吳龍翰)子霞舉,字孟陽,號默室。穎悟特早,首學《易》,師胡玉齋。 李偉,字敬叔,祁門人。少穎異,師同郡胡方平。 程曈《新安學系錄》之《新安學系圖二·朱子》,於胡方平之下即收有吳霞舉。《(弘治)徽州府志》又載胡方平“嘗館於休寧之新洲”。關於胡方平生平,說僅及此。餘皆不詳,待考。 二、影鈔元刊本與自序 《易學啓蒙通釋》初刊於至元二十九年壬辰(),且初刊本尚存。據上文董真卿所云,《易學啓蒙通釋》應有至元己丑胡方平自序。然無論是日本尊經閣文庫所藏至元壬辰刊本,還是致和元年(),福州環溪書院覆刻至元本,均不見胡方平自序,只載初刊時劉涇、熊禾二跋。至明代,此書有據至元書板重修刻本,亦有據至元本重刻本,入清後又有《通志堂經解》本、《四庫全書薈要》本、《四庫全書》本,皆無胡方平自序。朱彝尊《經義考》甚至誤將書中朱熹《易學啓蒙》原序當作胡方平自序,而四庫館臣則認爲董真卿記載有誤,至元己丑並非方平作序之年,實乃熊禾、劉涇刊書作跋之年。然據今存熊、劉二跋可知,刊書作跋均在至元壬辰,與己丑作自序並不衝突。潘雨廷對此有所辯駁: 一桂門人董真卿,云方平於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自序此書。考一桂於宋理宗景定五年領鄉薦,其年十八,則至元己丑年爲四十三,父方平之年當在七十左右。序此書後,一桂即以示於劉涇、熊禾等,乃刊於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刊書之年,劉與熊皆作跋,今皆存。惜方平之自序已佚。而《四庫提要》曰:“己丑乃禾與涇刊書作跋之年,非方平自序之年,真卿誤也。”未是。蓋真卿未誤,己丑實爲方平自序之年,亦爲一桂示書於劉與熊之年,是年方平尚在人間。而涇與禾刊書作跋之年,當在壬辰。故方平一身已當宋、元之際,謂之宋人固宜。然如通志堂之編次,竟置此書於項安世、鄭汝諧之前,則有近百年之差。而《四庫》反疑真卿之言,未深考耳。 潘文批駁四庫館臣之說,可謂有理有據,然言及自序及刊書事,則多爲推論。看來如果無法找到這篇自序,就不能解決個中紛亂。 其實關於胡方平自序問題,于義芳《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經部書叢考(四則)》已有所辨。該文提及北大館藏日本享和二年()刻弘化三年()杉原直養增刻《通志堂經解》本《易學啓蒙通釋》收有這篇自序,杉原直養卷末有跋云: 此書原係《經解》本重鐫,然訛脫不尠。天保甲辰夏日,俾試員就影鈔元刊本及朱子《文集》、《語類》等校訂,且併鈔本所載胡氏自序、熊禾跋文補刊。 跋中所云影鈔元刊本,即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清原家家學書》之一,係“日本重要文化財”,據稱係室町時代學者清原宣賢(-)親筆書寫。清原宣賢致力於儒學,曾擔任皇室講官,抄寫過多部經典。此本二卷二冊,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注文低一格,行二十字;小注低二格,雙行,行十九字。此本行款格式及內容與至元刊本基本一致,可見所據底本當出自至元本系統。惟卷首劉涇、熊禾二跋前,多胡方平自序一篇。今據此本錄其全文如下: 《易本義》一書,闡象數理義之原,示開物成務之教,可謂深切著明矣。《啓蒙》又何爲而作也?朱子嘗言《易》最難讀,以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必明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專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者設歟!象非卦不立,數非蓍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足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衍於蓍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且其間又多發造化尊陽賤陰之意,《易》之綱領,孰有大於是者哉!明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矣。然《啓蒙》固爲讀《本義》設,而讀《啓蒙》者,又未可以易而視之也。方平曾伯祖昂,政和間由辟雍第奉常,與韋齋先生有同邑同年之好。曾祖溢,紹興初復繼世科,因伯氏交於韋齋,獲聞《河》、《洛》緒論,而與先師朱子則世好也。《詩》、《書》餘澤,迪我後人。方平蚤歲又幸受業於鄱陽介軒董先生夢程,繼師毅齋沈先生貴寶。毅齋實介軒上游,而介軒乃盤澗先生從子,得其家傳者也。盤澗受《易》於朱子之門最久,淵源蓋深遠矣。方平因得受誦是書,沈潛反復二十餘年,著爲《通釋》一編,以授兒輩誦習,庶由此進於《本義》之書,非敢爲他人設也。先覺之士,幸有以亮其非僭焉。己丑仲春中澣新安後學胡方平序。 據其自序可知,胡方平言己之師承家學甚詳,汪幼鳳《星源縣志》所撰傳記基本脫胎於此。胡方平在自序中表明其作《通釋》之目的在於“授兒輩誦習,庶由此進於《本義》之書,非敢爲他人設”,胡一桂亦曾提及這一點: 先君子懼愚不敏,既爲《啓蒙通釋》以誨之。 而《星源縣志》所云之《易餘閒記》云云,其實正是據胡方平自序之前半部分略加刪改而成。自序中“又未可以易而視之也”之前的內容,在《(弘治)徽州府志》及《新安文獻志》中題爲《書易啓蒙後》,尚作爲題跋處理,他書則多沿襲《縣志》錄作《易餘閒記》之文,朱彝尊《經義考》雖誤將朱熹《易學啓蒙》原序當作胡方平自序,同時亦收錄此節內容,稱爲“後序”。 胡方平自序後低一格,又有胡一桂題識一篇: 先君戊子冬精加修定是書,其時一桂《附錄》已成。明年春正月,命一桂攜書千里,拜考亭夫子祠下,證文獻於是邦。閱四月皈省侍,而先君已謝人間世矣。終天抱痛,追慕何極!舍弟天桂出先君遺命,拳拳斯文不朽之屬。且復更定序文一篇,乃絕筆也。一桂承茲付授,不敢失墜。辛卯九月,再入閩關,歷壬辰季夏,兩書錄梓皆成。是書感隨齋劉侯捐金造就之賜,永矢無斁。讐校之餘,謹次其事如左。六月望日男胡一桂百拜謹識。 于義芳文已據此題識將胡方平卒年明確爲至元二十六年(),此處不再贅敘。這篇題識敘述《易學啓蒙通釋》初刊始末甚詳:胡方平在至元二十五年冬修定此書,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亦成書於此時。至元二十六年正月,胡方平命胡一桂攜書入閩,參拜朱熹祠。一桂此行得與熊禾結識,二人於武夷山中論學,四月後方返鄉。此時胡方平已去世,自序乃其絕筆。爲完成父親遺願,胡一桂於至元二十八年九月再次入閩謀求梓行,得劉涇資助,次年六月刊成。 關於胡方平修定《通釋》一事,於胡一桂著作中可窺一斑。其《周易本義啓蒙翼傳》“伏羲六十四卦方圓圖”下小注云: “卦氣疏密”一節,先人於《通釋》先天卦圖下論之已詳。但初藁謂卦氣盈縮蓋亦有說,且即內八卦以推十二月之卦,坎、離,陰陽之中者也,又爲日爲月,周於一歲十二月之間,故坎、離各八卦不當月分,所以疏密愈不同。後以坎離日月之說太新,削去不用。今看來離日坎月乃易象正說,共十六卦,又誠不當月分,未爲不可。故記於此,以相參考。 其中有“初藁”之謂。且今檢元刊本《易學啓蒙通釋》,的確已無離日坎月之論,可知所據當爲修定本。而關於刊書經過,亦有劉涇、熊禾二跋文可相佐證。劉涇跋云: 一日,約无咎詹君、退齋熊君訪雲谷遺跡,適值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易學啓蒙通釋》一編見示,謂其父玉齋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時熊君以《易》學授兒輩,謂是誠讀者不可缺之書,因言庭芳再入閩,惟汲汲焉父書無傳是懼,且欲以見屬仰。惟一時師友游從之盛,重念先世問學淵源之舊,輒爲刊置書堂,以寓惓惓景慕之心,且以成胡君之志焉。 熊禾跋云: 己丑春,余讀書武夷山中,有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其父書一編,曰《易學啓蒙通釋》。其窮象數也精深,其析義理也明白。且其間有言先後天方位,暗與《圖》、《書》數合者,不符而同,然後知天下之公理,非但一人之私論也。茲因刻梓告成,輒述所見以識其後云。 其中劉涇跋所記,當是胡一桂第二次入閩之事。熊禾與胡一桂相交相知,乃“斯文異姓昆弟”,其文集中數次提到胡一桂入閩事,與前兩次相關者如下: 余讀書武夷山中,有胡君庭芳自新安攜一編書來訪。究其業,蓋自朱子,而尤粹於《易》。留山中三閱月,相與考訂,推象數之源,極義理之歸。書成,余已爲係語。……胡君曰:“諾!歸將考隸一經焉。明年春當赍糧武夷山中,以畢斯業。”…… 君初來洪源三月,再自洪源遊雲莊又十月。…… ……紫陽有學子,綽綽醇儒姿。手攜圖象編,來叩文公祠。爲我再月留,着意窺精微。……今晨出別語,愴然敘心知:“家君授余學,感子爲發揮。母塋有雙湖,築室吾將依。願子識一語,晨昏奉無違。”聞君陳大義,臨分重含悽。…… 其中可與胡一桂題識相印證者:一桂留武夷山中三月之久,題識言出行往返共四個月;初次來洪源留三月,再次來又同遊雲莊共十月,題識言辛卯九月往閩,次年季夏書刊成,亦共十月;一桂初入武夷,臨別時尚不知父親已故,與熊禾約定次年春再來,而實際則是兩年多之後方成行,當是在家鄉處理父親身後事並守孝。 影元鈔本雖與至元刊本同一源流,然所據抄寫之底本卻並非至元刊本,差別除多一篇自序外,其內封忠實抄錄了底本原貌:中間題爲“新刊文公易學啓蒙通釋”,上有“錦江精舍”四字,書名之左右各有兩行小字,云: 《啓蒙》四篇,子朱子發明象數義理,深有以見其實而造其微。今復得新安玉齋胡氏援引諸說以爲《通釋》,誠讀《易》者不可闕之書也。敬用刻梓,以廣其傳。幸鑒! 錦江精舍應當是某書院或書坊,但名聲不響,亦未聞有所刻他書。且錦江精舍刻本今已無傳,甚爲遺憾。當然,我們也有理由懷疑,自序出自錦江精舍偽造,否則爲何初刊本、覆刻本、明修本皆無唯獨此本保留呢?然其內容多可得以印證,且偽作此序對錦江精舍而言似乎意義也並不很大。抑或因自序置於全書最前,本易失落,至元本書板丟失此序,而留存之刊本自序亦殘,惟獨據至元刊本新刊之錦江精舍本保留此序,流傳至日本後,清原宣賢據之抄錄一帙,幸得保存下來。鑒於自序保留有眾多信息,姑且寧信其有。 三、《易學啓蒙通釋》之新安槧本 《易學啓蒙通釋》自至元二十九年刊行於熊禾武夷書室後,致和元年()曾由福州環溪書院覆刻,版式一仍其舊,唯劉涇跋文末題改作“致和戊辰季夏朔環溪書院重刊謹跋”。此本日本東京都立圖書館有藏,卷中有“礪山宋氏世家”、“有不爲齋”等印,可知舊時曾先後爲朝鮮礪山宋氏及伊藤介夫所藏。至明代又有據元板修補本和重刻本。至清代,《通志堂經解》亦據元刊本重刻,而《四庫全書薈要》與《四庫全書》則又以《通志堂經解》本爲底本,其中《四庫全書薈要》曾據元刊本等校勘,糾正《通志堂經解》本錯誤數則。以上諸本與前文所論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影元鈔本,均出自至元刊本一系。 《通志堂經解》本《易學啓蒙通釋》納蘭性德序又云:“是書新安舊有槧本,今已不可得。”其所云新安槧本,即胡氏後裔於明末在婺源所刊之本,當時胡氏父子《易》學三書皆有刊行。至清代,刊本已殘缺不全,字跡漫漶,又有裔孫胡紫園及其子錦川、華川相繼取《通志堂經解》本校勘家藏本,於嘉慶十七年刊成此書。是則新安槧本又有明末刊本與嘉慶刊本之分。嘉慶本卷首姚鼐序及卷末余鵬摶附識敘此次刊刻始末頗詳: 姚鼐《胡玉齋雙湖兩先生易解序》:“胡氏三書舊於婺源有雕本,今皆殘缺,而昆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則三書具存。玉齋先生有裔孫紫園,取家藏殘本與通志堂本校其異同而擇從其善,復刻此三書於婺源,未竣而卒。其子錦川、華川繼成其美,以之示余。余欣紫園父子能闡揚其先祖之美,又冀是書流傳天下,士君子有志於學《易》者,慎毋舍此而他騖也。遂爲序之。” 余鵬摶《重刊易學啓蒙通釋附識》:“明季,先生裔孫烈徵、錦鰲、之珩諸人續刊是書,歷年茲多,字畫漫漶脫誤,難以枚數。近徵裔錦川、華川昆仲承先人紫園太守公遺志,編訂藏本,欲廣其傳。得昆山徐氏所刻通志堂本,及諸《易》書援引之說校之。” 可知明末刊本出自裔孫烈徵、錦鰲、之珩等人之手,今未見,惟據著錄知清華大學圖書館、安徽圖書館尚存有明末胡之珩刻《周易本義啓蒙翼傳》,半頁九行,行二十二字或二十一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有刻工。《通釋》之行款格式抑或仿此。關於明末刊本與至元刊本差異,雖其本已不存,然可據校勘者之一余鵬摶所撰附識窺其大概: 摶與斯役,次第審證。舊本集說詳核,每條以己說附諸儒後,想寓折衷示謙之意。通志堂本移玉齋說居前,其引諸儒處間有刪節,體裁較善,惟以朱子《啓蒙序》爲《通釋序》,頗見謬誤。按,通志堂本載劉氏及退齋熊氏跋,其書即仿劉所梓者,彼此俱源於閩,而移置刪節同異竟未能詳。茲就兩本刊補錯脫而擇從其善,註釋移前,俾順閱者之目,其集說并附圖仍舊焉。《啓蒙》原書分上、下二卷,《通釋》因之,雙湖《翼傳》“河洛”條小注甚明,舊本誤分爲四,與通志堂本異,竝行更正。 所謂“舊本”,即明末新安槧本。此本在形式上改變舊式,分兩卷本爲四卷,每篇爲一卷。就其文本而言,出入更大,其集說部分每條均將胡方平語附於諸儒之後,且引諸儒語多於通志堂本。余鵬摶認爲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通志堂本在集說次序上有所移置,將胡方平說移到前面;同時引諸儒說時進行過刪節。余文稱明末新安槧本與通志堂本俱源於元刊本,然通志堂本乃據元刊本所刻,除版刻錯誤或者修正底本誤字外,並未進行過所謂移置刪節之類的改動,取通志堂本與至元刊本相較,一看便知。 據附識可知,嘉慶刊本應當保留了明末刊本諸多特色,今取以觀之。是本內封左上題“嘉慶壬申年重鐫”,左下題“慶餘堂藏版”;卷端題“新安明經後學玉齋胡方平通釋”,卷末題“裔日照錦川、日章華川校刊”;卷首有嘉慶十五年八月姚鼐序,序末題有“金陵劉文奎局鋟”,可知此序出自劉文奎刻板之《惜抱軒文集》;次胡方平自序;次胡次焱序;次校訂姓氏;卷末收劉涇跋;次熊禾跋;次嘉慶十二年臘月王筆幟跋;次嘉慶十七年秋余鵬摶附識。此本所收之胡方平自序,至“又未可以易而視之也”即止,也正是所謂“易餘閒記”或《書易啓蒙後》部分,末題“開慶己未端陽前一日新安胡方平書於明經書院”,可見刊行時未得胡方平至元己丑更定之序,更不知尚有戊子冬精加修定之舉。若開慶元年()乃初藁完成時間,倒是與自序所云“沈潛反復二十餘年”頗爲吻合。胡一桂題識曾云其父“復更定序文一篇”,則這部分內容很有可能便是更定之前的序文,附於初藁。余鵬摶因未見自序全文,於是根據此序對胡方平卒年及成書時間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開慶己未書成,未板行而先生歿。元至元己丑,子雙湖先生一桂謀梓於閩,壬辰夏建陽劉君涇始付刊行世,蓋距先生成書之日已三十餘載矣。 嘉慶刊本於胡方平自序後,又收錄胡次焱序一篇。全文如下: 世之爲《圖》、《書》說者,何紛紛乎!彼惟於十數中求所謂八卦者,而見其夐不相干,於是創說以強通之。幸有一節偶合,矜以自喜,而於他節不合者,輒變例易辭,牽挽傅會,抑勒之俯就其說,雖穿鑿支離不恤也。余嘗以平易之說求之。竊謂《圖》者奇耦數而已,天一爲奇,地二爲耦,三、五、七、九奇之積,四、六、八、十耦之積。故一、二爲奇耦之始,五、六爲奇耦之中,九、十爲奇耦之成。一與二,三與四以至九與十,奇耦之相得也。一與六,二與七以至五與十,奇耦之有合也。天下之數,不出乎奇耦兩者。聖人於極儀象卦之理,默會於心久矣,於是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而有見於《圖》之奇耦,與吾心極儀象卦之理犂然有合。遂則其天一畫奇,是爲陽儀,而陽卦奇出焉;則其地二畫耦,是爲陰儀,而陰卦耦出焉。斯兩儀也。於兩儀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爲畫者四,斯四象也。又於四象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爲畫者八,斯八卦也。由是衍之爲十六,爲三十二,爲六十四,以至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以至無有終窮,皆自一奇一耦衍之。所謂“即《圖》畫卦”者,如此而已矣。不特此也。七、八、九、六,易所謂四象。內之一、二、三、四也,四象之位;外之六、七、八、九者,四象之數。《圖》之外,七南八東九西六北,此成數之四象;《圖》之內,一合五爲六居北,三合五爲八居東,二合五爲七居南,四合五爲九居西,此生數之四象。筮用其全,故七、八常多;易取其變,故七、八不用。積生數之一、三、五爲成數之九,乾用之;積生數之二四爲成數之六,坤用之。所謂“即《圖》畫卦”者,如此而已矣。何必執泥四方,強配八卦,而規規曰:“此屬乾坤坎離,此屬震巽艮兌。”至其窒礙牴牾,則嘔心斷腸,巧辭牽合,棄坦途,行荊棘,何乃自苦如此!吾叔玉齋先生於眾言殽亂中尊信《啓蒙》,爲之訓釋纂注,明白正大,具有淵源,隱然足以折近說之謬,而朱子賴以顯揚,於余蓋老友也。余嘗爲注述,舉前說質之,玉齋曰:“此所謂言近指遠者,而吾注偶未及之。請書爲序。”余曰:“玉齋此注,足以闡明朱子之書;次焱此說,足以翼附玉齋之注。”遂書之不辭。 族子梅巖次焱謹序。 胡次焱字濟鼎,號梅巖,晚號餘學,婺源人。宋亡後奉母教授鄉里,有《梅巖文集》十卷傳世。胡次焱與胡方平父子均有交往,又有同宗之誼。此序又見於其文集,題曰《啓蒙通釋序》。此序主要是與胡方平進行學術討論,補其書之不足。撰序時,胡方平尚在人世。胡次焱另有跋文一篇收在文集,題爲《跋胡玉齋啓蒙通釋》,諸本皆未收,其文如下: 宗家耆英,有以玉齋自號者,名方平,於予爲老友。其子雙湖,於予爲益友。此書玉齋所著也。歲己丑,雙湖攜入閩鋟梓,留滯踰一年。辛卯秋再往,明年壬辰夏季回,留滯過一年。冒寒暑,疲跋涉,必成父志,乃已允謂孝矣。弛擔云初,首惠此本。嘗復其書曰:“玉齋平生精力,寓於此書。儻非繼志述事不懈益勤,未有不墜於泯滅無聞者。是故貴有子也。”十年前,嘗跋《輶軒唱和詩集》,極言有子無子之效,於今益信。嗟夫!談《史》以遷顯,彪《史》以固顯,故曰:貴有子也。然此史學也,非經學也。充《禮》以裒傳,曾《書》以祉傳,故曰:貴有子也。然此《書》、《禮》學也,非《易》學也。乃若梁丘賀之有臨,劉昆之有軼,張興之有魴,伏曼容之有暅,《易》學傳家,父作而子述之,赫乎相映,故曰:貴有子也。夫《啓蒙》者,入《易》門戶也。玉齋既爲《通釋》,雙湖又爲《本義附錄》,非惟橋梓相映,楂棃兼美,且將突過煙樓,此又賀臨以來所無者。嗟夫!箕裘失墜者,固不足言矣。其或苟安憚煩,無以張皇先美爲不朽計,雖讀父書,亦無取焉。古今嗜學著述如玉齋者豈謂盡無其人,無雙湖爲之子,遂使潛德弗耀,抱恨幽宮,雖謂之不孝可也。有是父,有是子;有是子,有是父。或曠百載纔一遇爾。吾於雙湖此舉,敬歎無射。其中大義奧旨,尚遲締玩。嘉羨之劇,亟題此卷端,庋置几間,俾有目者必觀,有識者必羡。非徒贊揚雙湖,亦以動天下之爲人子者。併書一本,寄雙湖云。七月辛巳宗末次焱濟鼎敬跋。 此跋雖未標明寫作時間,然據其內容,當撰於至元壬辰夏胡一桂自武夷刊書歸來之後。而胡次焱本人嘗在《跋朱伯純程文》一文中亦提到: 十年前歲壬辰,予跋胡玉齋《啓蒙通釋》,極言有子之效。 可知此跋作於至元壬辰七月辛巳。此時胡次焱得胡一桂所贈熊禾、劉涇刊本,心生感慨,故手書跋文一篇於其卷端,併寄送胡一桂一份。因係刊後所撰,此後歷次刊行亦未能收錄。嘉靖中,其孫胡璉搜輯詩文,爲之編定爲《梅巖文集》十卷,胡次焱爲《易學啓蒙通釋》所作序、跋皆收入其中。此跋所載《易學啓蒙通釋》初刊始末,與胡一桂、劉涇、熊禾之序跋亦基本相符,惟所云“歲己丑,雙湖攜入閩鋟梓,留滯踰一年”,與歷時四月之事實頗有出入。不過胡次焱雖與胡氏父子同在婺源,然一居考水,一居梅田,並非朝夕相處,記載偶有疏漏亦在情理之中。在跋文中,胡次焱對胡一桂不辭勞苦盡心完成父志之舉極爲贊賞羡慕,認爲如此父子“曠百載纔一遇”。 經過與元刊本進行文字比勘,嘉慶刊本多出許多條目,有近四十處,多爲援引朱子之語,間有潛室陳氏、程子、西山蔡氏說,此即余識中所云“茲就兩本刊補錯脫”者。其中有數條引自“黃氏瑞節”,最是令人愕然。按黃瑞節字觀樂,安福人。延祐四年()舉於鄉,嘗爲連州學正。黃瑞節輯編有《朱子成書》十卷,其中收錄《易學啓蒙》,瑞節亦搜集眾說以申其意,並附錄己說於後,體例與《易學啓蒙通釋》相類。黃瑞節之生活年代顯然晚於胡方平父子,且《朱子成書》初刊於至正元年(),《易學啓蒙通釋》又如何能夠引用其說?今據嘉慶刊本略加調整,將余識所謂移置最前之胡方平語改置最後,借以大致推想明末刊本原貌。然調整之後,竟與明初胡廣等人奉旨編纂之《性理大全》卷十四至十七所收《易學啓蒙》集說部分如出一轍。按《性理大全》之《易學啓蒙》,先錄其原文,並集宋元諸儒之說於後。而在實際操作中,胡廣等人則是充分利用了前人成果: 明初纂修的《性理大全》,其中卷14至17爲《易學啓蒙》,將方平的《易學啓蒙通釋》除了極少數的刪節外,全書收入,只不過另外再補上一些朱子、蔡西山、黃瑞節等人的言論而已。 可見《性理大全》是將胡方平《易學啓蒙通釋》略作刪節,幾近全書照錄。而所謂另外再補的“朱子、蔡西山、黃瑞節等人的言論”,其實也並非胡廣等人所集,均出自黃瑞節《朱子成書》。綜上,我們有理由懷疑,明季胡氏後裔刊刻《易學啓蒙通釋》時,其實並未找到此前任何一種刊本,而是直接將《性理大全》相關部分錄出,刊爲一書。而《性理大全》往往將“黃氏瑞節”置於“玉齋胡氏”之前,胡氏後裔因過於迷信《性理大全》,對其中所引黃瑞節語竟未作任何考訂,一律照搬。此本家刻家藏,以致二百年後仍舊貽誤後人。平心而論,嘉慶刊本經紫園父子三人延多人參與校勘,前後歷時五年,其文字不可不謂精善,惟未能勘破家藏舊本之秘,沿襲其誤,委實可惜!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5輯,北京大學出版社,。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 长按识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ianzixina.com/lzxsljz/8932.html
- 上一篇文章: 听说隆昌源早餐上新啦走,去看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